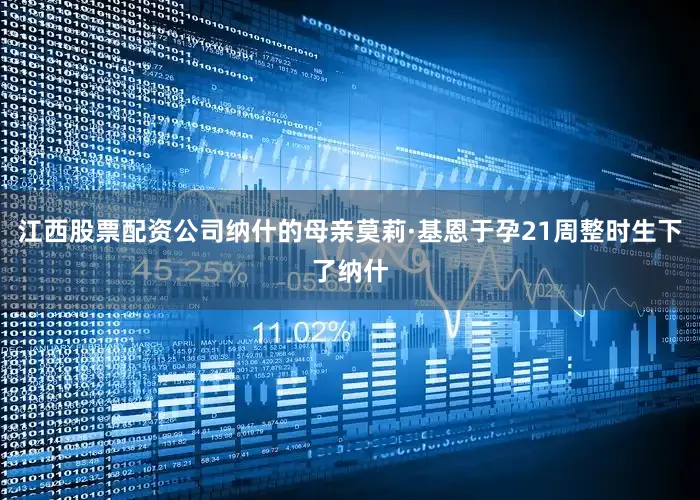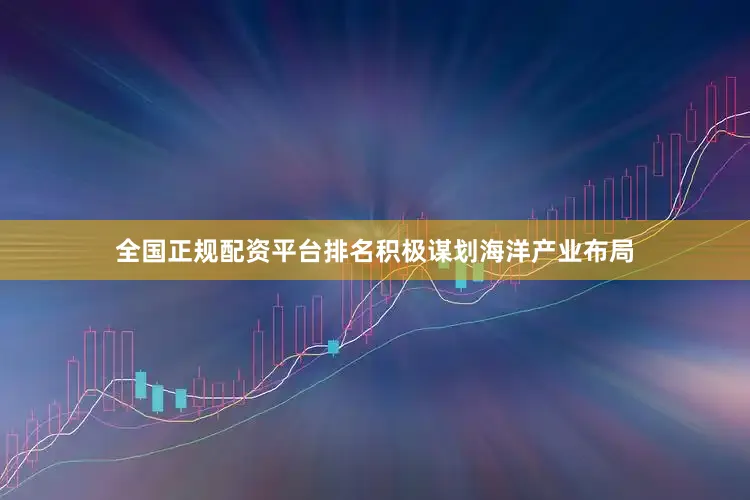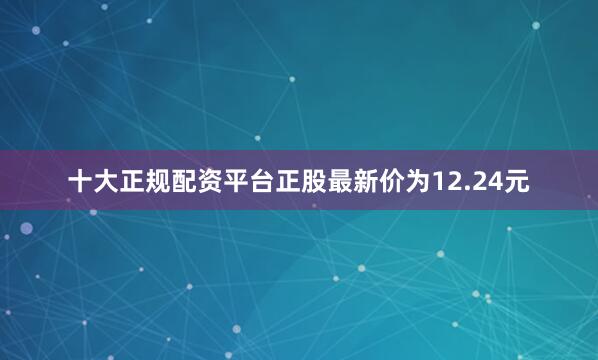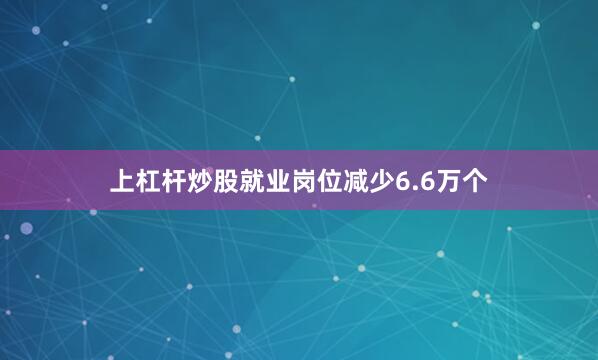川味文化作者:泡海椒
导读:
√ 老南京川菜概说
√ 南京外帮菜前情
√ 蜀峡饭店之历程
√ 南京川帮之崛起
注:文末附有三十年代初,蜀峡带领大小川菜馆在报纸上刊登的集体广告,其阵仗纵使放到今日,也不多见,足令吾川菜业同仁为之鼓舞。
(一)老南京川菜概说
川菜登陆南京市面,要比在上海和北京来得晚一些。
民元初,上海出现式式轩酒馆,是年冬,北京诞生瑞记饭庄,由此拉开两地川菜序幕。历十余年发展,至二十年代中,两地川菜事业同时迎来第一个高峰,川馆林立,川厨争雄,名店名师遐迩著闻,名菜名点脍炙人口,一跃而为当地饮食界举足轻重的帮口。
而在南京,直到国民政府奠都后,才有川菜馆现身,较前述两地晚了15年之久。即便如此,南京的川菜声势,不但不输上海、北京,就是同川菜大本营成都、重庆相比,也毫不示弱。

下列数据,由笔者不完全统计所得,以见老南京川菜局面之一斑。
自1927年至1949年,南京有名可考的川菜馆达82家,包括以筵席宴会为主的大餐馆,如蜀峡、浣花、皇后、益州等;以零餐便饭为主的小吃馆,如约而精、豆花村、新民、桃园等;以面食点心为主的面食店,如富华春、菜羹香、经济、顺兴园等;以及标榜火锅的四川毛肚大王、怡乐园、巴山、五味和诸馆。
同时,兼营川菜者有13家,其中不乏大名鼎鼎之辈,如综合型的中央饭店、国际饭店、环球饭店,主打粤菜的安乐酒店、世界大饭店,本帮老字号金陵春,浙绍帮的六华春,以西餐著称的撷英、金陵咖啡馆、小巴黎、好莱坞等,都曾应市场需要经营过川菜。
此外,尚有9家经营川味特产的食品商店,有的制售四川泡菜、大头菜、铳辣菜、川式豆豉、豆瓣酱、川味香肠腊肉、银耳山货之类,如川香远、峨眉、蜀丰等店,有的还附设有小食部或茶厅,兼办豆花、茶点、面食之类,如成渝商店、川产商店等。
综上合计,民国中后期22年间,南京涉足川味菜点的商家,至少有104家。再看成立时间,除1938至1945年的8年为新增空白期,其余每年都有新的川菜经营者出现,相当于开办104家只用了14年,这样的频次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,成渝以外,无出其右。
(二)南京外帮菜前情
川菜相对于南京本地风味,属外帮菜,而南京有外帮菜馆,实始于清末金陵设关。


早在1858年,《天津条约》议定南京为通商口岸,因其地为太平军所据,未能实行。直至1899年5月1日,金陵关才举行开关仪式,正式宣布设为商埠。嗣后,西餐随洋船、洋人、洋货入宁。
1900年,时任护军统领的杨境岩军门,为款接外宾,集股创办金陵春公司,于贡院前开设金陵春番菜馆,派胡宾秋经理,为南京西餐馆之先。1903年,江南第一楼设于下关江边,继起者有悦生公司、东惠春、润昌、永和、江南春、涵万楼、金陵村等。各家虽以番菜为号召,但均兼售中餐,有的还设有茶馆、烟室,甚至在明令禁止下,仍恣意代客招妓。这种中西合璧的经营方式,对后来南京菜馆业影响颇深。
当时的中餐馆,统称华菜馆或中菜馆,多由南京、苏州、扬州、镇江、无锡、徽州等地人操办。1909年,名店有问柳、琳琅新馆、三柳居、大兴楼、斌园、新太和馆、清饮楼等。1914年,继增长松园、长松东号、海洞春、老万全、文明雅集等。若以食俗而论,各家皆可称江南风味,故内部或有商帮之别,而于外则尚无风味细分。
1916年以后,南京中餐馆才又有了些新气象,先是北京帮在府东街开山东馆,其后广东帮在下关二马路设粤华楼,又于姚家巷口置群乐楼,业界始有南北两帮。原来笼统的江南风味,内部也开始细分,至1926年,市面已有京苏馆(指南京馆,亦称本地馆)、扬州馆、苏锡馆、浙绍馆、徽州馆、京馆(指北京馆)、广东馆及西餐馆、教门馆、素菜馆之分,久华楼、老万全、魁星园、无锡馆、百利等家即各帮代表。
1927年4月18日,国民政府奠都南京,各界人士汇集金陵,机关林立,人口骤增,大小菜馆应时而起,不仅数量远多于前,风味亦日趋丰富,续添湘、闽、津、豫、川、滇、黔等各省菜馆。
(三)蜀峡饭店之历程
南京首批川菜馆,创于1927年底至1928年初。现知第一家为民生餐室,店设成贤街。其后,又有鼓楼黄泥岗的四川民众食堂,碑亭巷的农家味川菜馆,皆属小吃馆。或因规模有限,又偏居城北,三家馆子并未造起太大声势。


1928年3月27日,蜀峡饭店在府东街正式开幕,南京川菜馆才算有了第一个扛把子。相较民初上海、北京川菜先驱的古色古香,南京的蜀峡则处处透露着新鲜气息。
一是名号新。饭店一词,原是对西式旅馆的称呼,尤指同时提供食宿综合服务的大型旅馆(我国自古也有饭店一说,但内涵与近代饭店不一)。此前的南京,惟英商百利、南京花园等以饭店称,且各家都以旅馆为主要。蜀峡为一大餐馆,只做饮食,并无住宿等业务,以饭店缀名,至少在南京可称先行者之一。
二是选址新。蜀峡店址并非独立门店,而是附设于府东街青年会——全名南京基督教青年会(碑亭巷另有女青年会),在教会场所开川菜馆,这是前所未有的。南京青年会萌芽于1909年,1912年在王正廷、唐绍仪、曹复赓、马伯援等人支持下正式成立,会址初设花牌楼,孙中山曾捐助3000元作为开办经费,并出席成立仪式。1925年,该会又于府东街繁盛地段新建会所,翌年建成迁入。
蜀峡开幕时,房屋尚新,倚青年会营业,优势得天独厚。一方面,该会所在的府东街,后改建中华路,自古为金陵南北要冲,历史悠久,交通便利。另一方面,当时青年会会员逾千人,时常往来会所间,仅此人流量便相当可观。何况会员中尚有各方要员,人脉宽泛,交际频繁。会所周边更遍布机关、会馆、银行、学校,客源极富。蜀峡此举,想必不是无心插柳。



三是组织新。蜀峡由多方合办,既有方致和等川籍人士,又有张如山等南京业界老手,且幕后另有某实权人物(笔者仅握孤证,暂不贸然列出)。川菜馆由四川人牵头,于厨师招募、原料供应、出品把控自有得月先机。而南京资深业者加盟,对蜀峡乃至川菜在南京本地化经营,更有极大推动,张如山后来就参办都益处、西南酒家两大川菜馆。
四是模式新。此前,笔者曾谈到早年川菜馆的经营模式,有专门、主营、兼营几种,主营模式中,店家常以川菜为主,间或兼营其他地方风味菜点。但蜀峡主营川菜的同时,竟兼营西餐,再开业界先河。这一做派,从近代南京菜馆业的角度看,是对清末中西合璧的继承,蜀峡模式后被一些大川馆沿用,又称得上是一种发扬。
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俱备,蜀峡的经营者进而决定走高价路线,把普通席定在二十元左右,较一般菜馆的高档席仍胜一筹。全新的蜀峡立于金陵城中,令人耳目一新。时值新都初定,那些激荡着新思潮,开创着新局面,又有消费能力先生女士们,不仅没有望高价而却步,反而对其抛撒出巨大热情。
蜀峡甫一开幕,便迎来满座高朋,李登辉、张伯苓、曾熙、谭延闿、邵力子、胡汉民、戴季陶、孙科、王正廷、邢士廉、王树翰、何应钦、韩复榘、石友三、许世英等人先后造访,使得蜀峡名声大震,门庭若市。两年后,原有场地已不敷应用,遂另择新址以扩充经营。
1930年3月14日,蜀峡饭店迁至新街口糖坊桥43号营业,新店设施更齐备,装饰更堂皇,服务更周全。内设新式礼堂,可承办大型会议、婚礼。大小包房数十间,能同时举行多场宴会,房间不仅精美,还备有化妆物品与四时花果,可谓细致入微。至于厨上,则仍由四川名师主理,细心研究,调和食品,中西大菜,应有尽有。


糖坊桥在新街口东北隅,毗邻新都建设中心,巍楼耸立,银行聚集,更具现代气息。此时的蜀峡,也更具大家风范,常承办各种全国性大会、新闻发布会及各类团体聚会,夜以继日迎送各地来宾。汪东、仇鳌、蔡元培、罗家伦、贺耀祖、曲吉尼玛、徐悲鸿、徐志摩、朱培德等人都曾在此落足,黄侃、邵元冲更多次光临,陈调元竟因垂涎蜀峡的炒菠菜、烧粉丝两菜,直由安乐酒家转战于此。
1930年7月20日,四川旅京同乡会在蜀峡饭店正式成立,数百名川籍同乡济济一堂,同叙乡情,共谋发展。该会由前南京全蜀会馆改组而成,向为川人交流互助的重要组织,此番承办成立大会,一举奠定了蜀峡在南京川帮中的地位。
1931年中,蜀峡饭店面向社会公开招股,组织成立股份有限公司,增加资本,自建三层洋楼,进一步扩充营业,并举郭仕鲁任经理。是年底,上海蜀峡饭店在三马路开业,这是南京川菜又一重要时刻。三十年代,上海川菜对南京影响巨大,名店、名厨输出极为频繁,而蜀峡由宁至沪,是为南京川菜异地扩张之发端。
1933年秋,蜀峡由盛而衰,究其原因有三:一是糖坊桥一带市政建设,蜀峡陷入土地纠纷,影响经营;二是浣花、益州、皇后等新一批川菜馆崛起,蜀峡失去一家独大的优势,生意渐落;三是资金既不足,债务亦沉重,而蜀峡收购天天酒家失败,引发官司,雪上加霜。是年冬,蜀峡饭店宣告歇业,翌年被法院查封,以抵偿债务。


(四)南京川帮之崛起
蜀峡饭店谢幕,南京川菜馆却因之而崛起。
1929年初,当蜀峡方兴未艾之际,川菜筵席渐为新都仕女青睐,早期开设的民生餐室与农家味,因未能及时调整策略,不久便推盘他人。但四川民众食堂,却乘着蜀峡掀起的声浪,由专攻小吃转而进军筵席,并大获成功,后一直持续经营到抗战前夕。
1929年夏至1933年夏,在蜀峡鼎盛之时,一大批川菜馆顺势兴起,五东、西南、又益处、新生活、峨嵋、都益处、小进步、昆仑、蜀南、豆花村、新都、乡味斋、浣花、益州、皇后、约而精、随园、春风小啜楼、碧峡村、浴春江……大小30余家川菜馆遍布全城,并形成中山路、夫子庙、黄泥岗三个相对集中地带。
三十年代初,日贼犯华,社会上下,节衣缩食,共赴国难。蜀峡饭店提倡经济小吃,推出廉价客饭,并免除加一、小账、茶饭等额外收费,这些举措得到大小川馆纷纷响应,各尽己所能及之力。
四五年间,南京川帮已初露锋芒,即将迎来群雄逐鹿的时代。


本文系“消失的川菜名店——老南京川菜馆”系列之一
部分图片来自网络,仅供示意
转载须经本人同意且注明:川味文化・泡海椒
看川菜老传统,听川味龙门阵
间群策略,炒股配资代理,配资178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